雖然這篇introduce介系詞鄉民發文沒有被收入到精華區:在introduce介系詞這個話題中,我們另外找到其它相關的精選爆讚文章
在 introduce介系詞產品中有19篇Facebook貼文,粉絲數超過1萬的網紅盧斯達,也在其Facebook貼文中提到, 【盧斯達:黎明狙擊光榮冰室,是打擊運動道德高地還是太沉迷自抬身價?】 在教育大學任職社會學講師的上海人黎明,對光榮冰室攻擊一浪接一浪。早前黎明與丈夫鍾一諾寫信給《刺針》,暗示光榮冰室在疫情下「不招待普通話食客」有歧視之嫌;其後黎明繼續狙擊,找了幾個「港漂」一齊去光榮冰室,全程用普通話點餐,「找尋對...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41萬的網紅TGOP (This Group Of People),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有習慣的口頭禪,口頭禪也是讓朋友更加快速連結人物的關鍵,但是往往你能想到的都是那幾個特殊詞。這群人經典語錄系列這次將為您介紹一些以“幹”.“靠”.“哭”.“喔”.“最好”.“屁”為主題的口頭禪,這些早已融入年輕人生活之中口頭禪是不是覺得很耳熟?看完還不趕快標籤您身邊中槍的朋友。 ...
-
introduce介系詞 在 TGOP (This Group Of People)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2016-04-15 08:00:00日常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有習慣的口頭禪,口頭禪也是讓朋友更加快速連結人物的關鍵,但是往往你能想到的都是那幾個特殊詞。這群人經典語錄系列這次將為您介紹一些以“幹”.“靠”.“哭”.“喔”.“最好”.“屁”為主題的口頭禪,這些早已融入年輕人生活之中口頭禪是不是覺得很耳熟?看完還不趕快標籤您身邊中槍的朋友。
There are some catchphrases that everyone uses in their daily lives. Certain catchphrases are also easier to be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people, but often or not the ones people most commonly use are those unique phrases. TGOP Quotation Series will introduce how “fuck“, “damn“, “you better“, “bullshit“, and “oh“ are used in our everyday vocabulary. Do any of the phrases sound familiar? Tag a friend that also is guilty of using these phrases that just seem to roll off your tongue.
支持群人 訂閱訂起來➔ https://tgop.pse.is/GWAQ6
A Day To Remember 播放清單 經典語錄系列➔ https://tgop.pse.is/M3HAM
來看這群人更多日常生活 ➔ https://tgop.pse.is/KZPB2
群人製作的都在這➔ https://tgop.pse.is/KB5Z4
演出:網路搞笑團體「這群人」This Group Of People a.k.a. TGOP。
註:戲劇效果、激動演出。
請調整為1080pHD觀看品質較高。
片尾曲:Breakup Song ➔ https://goo.gl/bWcUOf
Translated by Jason Young
Facebook
這群人: https://tgop.pse.is/K7SE2
展榮展瑞: https://tgop.pse.is/MGXKV
茵聲: https://tgop.pse.is/LEVZ5
董仔: https://tgop.pse.is/MDX52
石頭: https://tgop.pse.is/LZS6Y
尼克: https://tgop.pse.is/HJB2Z
木星: https://tgop.pse.is/MC3JL
Instagram
這群人: https://tgop.pse.is/KE6S9
展榮: https://tgop.pse.is/MJER2
展瑞: https://tgop.pse.is/MEVXJ
茵聲: https://tgop.pse.is/KFWEX
尼克: https://tgop.pse.is/M4GAE
董仔: https://tgop.pse.is/MNY8W
木星: https://tgop.pse.is/KMBXE
石頭: https://tgop.pse.is/MSNET
這群人bilibili: https://tgop.pse.is/M79UP
這群人微博: https://tgop.pse.is/MLT7Q
【兩班半攝影棚開幕啦】
https://www.17hrs.com.tw/
【工作邀約請洽詢】
聯絡信箱 :thisgroupofpeople@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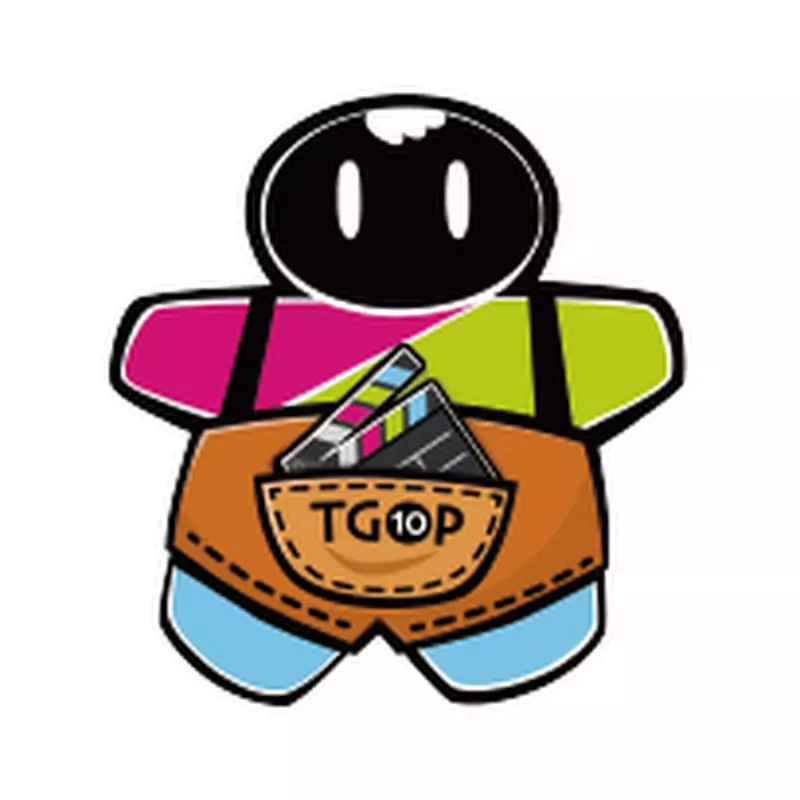

introduce介系詞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黎明狙擊光榮冰室,是打擊運動道德高地還是太沉迷自抬身價?】
在教育大學任職社會學講師的上海人黎明,對光榮冰室攻擊一浪接一浪。早前黎明與丈夫鍾一諾寫信給《刺針》,暗示光榮冰室在疫情下「不招待普通話食客」有歧視之嫌;其後黎明繼續狙擊,找了幾個「港漂」一齊去光榮冰室,全程用普通話點餐,「找尋對話的可能」。
侍應堅持自己不懂聽普通話,一班「港漂」最後亦等不到老闆「對話」,只放下防疫用品就離去。事後自導自演的黎明,煞有介事寫了三篇文講這個行動,並「總結」出「說什麽語言不重要,溝通得到就行」;正直可以解決一切仇恨,要守衛自己的心,切記不要對人「麻木不仁」。
黎明等人的行為,有以下若干問題:
動機不純,身位過佳——
光榮冰室事後發文,再三強調黎明一行人,全程講廣東話,而黎明則自稱說普通話,雙方的描述有事實差距,可能有一方說謊。不管如何,光榮冰室認為「放蛇」行動實在不必,「放蛇」確實描述精確。
黎明文章再三強調,「期待對話和解」,但問題是冰室早就說過,是因為政府不封關,店方就「局部封鋪」自保,並無歧視中國人,根本不需要和解,但黎明不斷說要「對話和解」,就表示她感覺受「不招待講普通話食客」的店家所歧視。在她的內心世界,這是「以德報怨」。
然而實際上,黎明是去踢館、踩場、放蛇,等著拿到冰室的黑材料:如果店員在過程中理解到普通話,黎明就會一口咬定冰室早前以「店員不懂得普通話」回覆平機會的歧視指控,是遁詞,平機會就可以「繼續跟進」,沒有跟進,她也可以嚴重打擊光榮冰室的誠信和道德光環。
平機會是在《刺針》文章刊登之後,開始找光榮冰室麻煩。冰室以「侍應不懂普通話」回應,黎明的行動罷明就是要去踢爆,坐實冰室歧視中國人種,而非關語言或者抗防的指控。黃店被黑社會搗亂打爛,都可以復修,傷害有限;但以「歧視」的高帽套下來,不斷纏擾,就水洗不清,而且可以連同親中的白左一齊發大,達到discredit香港整場時代革命的目標。黎明鍾一諾的《刺針》文章,何式凝兩次上外媒批評運動「很父權」、迫害她,都是這個discredit工程的一部份。
黎明鍾一諾的《刺針》文章刊出之後,受到不少批評,黎鍾當然受不了這種委屈,就希望放蛇製造證據出來,證明自己的疑似歧視指控,並非無的放矢,威返俾你睇,但放蛇行動失敗,侍應真的全程不懂普通話,只能叫他們手寫菜單,特殊處理;但黎明何其聰明,出擊只有大勝或小勝之分,拿不到黑材料,也可以將自己粉飾成一心對話、渴望和解的純情中國人。身位站到怎樣也贏,令人側目。
道德勒索 手足自助餐——
黎明不斷聲稱自己「也是」香港人,正如她也不斷聲稱自己「也是」手足。劣質中國人在外國,懂得鑽營各種社會福利和移民制度、透支外國人的無支和愛心,令自己利益最大化;黎明也懂得箇中三味,她利用時代革命來剝削香港人:你們不是說支持民主就是手足嗎?你們不是支持民主自由人權嗎?那你怎麼不接受我?為甚麼不能用普通話跟我說話?為甚麼不懂普通話?
這就好像一個強姦犯對妙齡少女說,平時妳樂善好施,上教堂也給十一奉獻,那為甚麼不獻身給我呢?妳不是崇尚大愛包容的嗎?
黎明的軟軟渾渾文研社會學風格文字,內裡卻是武裝的,是一種道德勒索,她主張「感受他人的痛苦並為其哀傷、與之同行」,她是這個主張的受益人,但她不會反求諸己,也付出。如果說手足就要互相包容、互相支持,那黎明只會接受自己被支持,而自己不會支持人當黎明不斷攻擊光榮冰室,鼓動無知和無父無君的無國界左翼去圍攻光榮冰室,以圖在國際環境和輿論界抹黑之,早就超過了共同體之間不割席的信條。自認手足?行開少少。
如果黎明真的不喜歡「不招待普通話食客」的規定,大可以私下與老闆探討爭取,而不是先出文去《刺針》篤魁,再放蛇做真人騷。明顯黎明並非真的在乎那個規定,而是要煮死冰室,並且抬拉自己的社會資本。因為常人都知道,公然如此挑機,我是老闆都不會理這種麻煩人,然後黎明又可以投訴,是對方不願意和解對話。
黎明玩的是「手足自座餐」,手足這個概念,有利益和著數的時候,就要,拿來勒索別人,但她明顯沒為光榮冰室著想。港漂一天到晚要求理解他們,他們卻極少共情香港人被剝削所有權力,只能靠天然方法抗疫的焦燥,也不反省普通話、中國人是殖民體系中具有權力的一方,香港人沒有義務在不平等的狀況下,強求一切一視同仁。
黑人對白人戒懼和敏感,有歷史和事實累積的敵意,白人不能投訴為甚麼黑人要視白人為「他者」,不是所有白人都是仆街——那就問問你的同胞,看看具體的權力結構,在現實政治都未得到和解的時候,要人民和解,不和解就是歧視,是著「不應區別對待」的教條勒索世人,是將婦女以「貞潔」之名浸豬籠處死。
港漂及高等中國人的陰暗心理——
不少中國人,面對香港都有這種想法:為甚麼西人到香港,香港人就轉channel講英文,我來,他們卻不遷就我講普通話?為甚麼西人就不需要融入,而我就要融入?
這個問題,大家都明,只有刻意不明白的人。英文對比普通話,在香港的普及歷史更長。現時市面四五十歲的人,可以真的不懂得。幾十歲的親中社會賢達,不少就完全是普通話有限公司。年輕人因為被普教中改造,反而說得比上一代好。
拿西人來比,只是去脈絡化的發脾氣。而且西人的數量、劣性、權力含金量,與普通話族群根本不能同日而喻。西人沒有講過「沒有中央照顧,你們完蛋」,沒有來走私、搶奶粉搶疫苗、沒有來散播病毒。尊重不是別人賜予,更不是可以勒索回來,而是要自己賺來。如果普通話人在香港感受到不友善,不要怪人,反求諸己,去怪自己的同胞長年累月搞成這樣。黎明班人去冰室尋求「對話」,曲折迂迴,但其實是霸王硬上弓,你走來踩場要跟我對話,不就是強迫嗎?手法如此粗暴,可見有幾多誠意;可見是在乎問題本身,還是自己想發泄。
黎明的東西折曲如此,因為自大和自卑交替運作。黎明在文中不斷說自己融入得好快,好幸運,但其一切行為,都是出於內心認為自己不被真正接受的怨恨,一種怨毒的反擊。即是一個美人不會每天煞有介事說自己是美女;一個已經歸化的人,不會一天到晚說自己已經融入,你看我融入得多快,你看有多少世界公民朋友看我抬戲,我真的完全不覺得自己和本土人有甚麼分別,我是手足,難道我不是手足嗎……
黎明在2017年寫東西,呼籲超越身份政治,但她每次都是標榜自己「來自上海」,這也是「身份政治自助餐」,有得上報就不超越身份政治;別人不接受普通話點餐,就認返手足認返香港人,又要求超越身份政治了。
黎明的行狀,其實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上世紀初以來,「南來文人」就是懷著一種高高在上的身份,來香港指點江山。他們一方面拿香港的東西,一方面又是看不起的。「文化沙漠」的概念就是南來文人的發明。魯迅也說過,英國不懷好意,保留了四書五經和傳統中國文化,是要用來奴役人民,對香港的印象很差。就像「外省人」逃到台灣,明明自己是難民,卻又看不起台灣本土人,內心的中國人優越感雖然實在,但無處承接,遺民也不世襲,是注定滅亡的,於是內心就只能走向與本土人對抗。
黎明的中國人優越感,只是用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確語言來包裝。當侍應試著用很爛的普通話來回答時,黎明馬上笑逐顏開:「不會啊,妳說得好好誒!」這便是一種教化蠻民的調調,如果香港人願意講普通話,她就感受到「香港人」的意涵倒向有利自己生存的一邊,自然高興;如果不行,她也可以扮演啟蒙民眾,令他們放棄「歧視」的自由派導師。這種賣直自傲的心理,骨子裡總是中國人的陰暗心理。因為自覺被歧視、自認是受害者,就生出一種「香港人需要我來教育」的心態。
利己主義無極限——
入鄉隨俗,是贏得群體尊重的第一步,但我看見個別支持黎明放蛇行動的左翼,卻連這個常識都質疑。絕對個體主義的人會認為,你要我隨俗,已經是入侵我的主權。那你有你繼續說普通話的主權,我也有我不招待你的主權,有甚麼問題?
一個地方的人,是否接受你,也是他們的主權。你可以努力,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那個地方的人手上。人與人的交往,不是加減乘除的遊戲,不是說你做了check list上若干東西,就自動獲得認可。當然蝗蟲型人類的學問,其深也密,他們首先勒索認同,如願自己製造了敵人之後,再擺出被迫害的樣子,繼續欺騙其他同情心過盛的凱子,坐穩天字第一號受害者的位置。既實現了受害者最大的身份政治,也愛護了自己內心放不下的高等中國人身份認同,他們就能演一個「我都很想融入香港但香港人不接受我」的苦主。然而很多東西都是他們自己招來。
很多中國人都想融入香港,他們低調而耐心,但多年努力可能一夕被黎明抹殺。很多人不是討厭港漂新移民,而是討厭像黎明沽名賣直、玩弄身份政治成精的政治綠茶婊。黎明做這種引起香港人反感的事情之前,有想想跟自己一樣的新香港人嗎?沒有,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就像來香港去世界胡作非為的中國人,只求一時之快,沒有想到自己的同胞一樣被黑。
然而說到底,相比起來,在香港街上大便的中國人,也真誠過黎明這類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大便掃走就是,但矯情兼攻於心計、販賣受害者形象、玩弄身份政治、製造混亂、製造了那麼多分化和事端,還感覺良好,毒性烈得多,持續的影響深遠得多。也許他們認為在這裡可以找到「絕對自由」,就是一個自出自入的雞籠,但我告訴你們,香港不是你們放肆的地方。
黎明的綠茶性格很深,注定她像何式凝一樣,她們做人只關注自己喜不喜歡,不會看群體和世界。群體有義務接受她們,她們永遠不理解現實。她自稱融入香港已經成功,因為「我的幸運也是和我的文化資本緊密相關的,如果我沒有對語言的興趣和學習能力,如果我不是來自上海這樣一個文化開放度相對較高的大城市,如果我的衣櫃裡一件符合這個社會審美眼光的衣服都沒有……那麽就算同樣於 2008 年來港,境遇和融入機會也會有很大不同。因而,我的幸運也是帶有階級性的。」繞這麼大個圈來讚自己,不用吧?
暗裡批判別人歧視,但她很小心將自己從歧視的對象分割出來,因為她是高級上海人,有文化資本,有語言能力,還有很多合時的靚衫,她已經融入,只是為其他被歧視的人疾呼,多矯偽,多麼無法面對真正的自己,多麼扭曲的心靈。
俗語說醜人多八怪,真正希望世界更好的人,說話不會那麼多關隘、行事不會有那麼多城府。設下了那麼多害人和收割光環的手段,再談守護自己的心、談運動、談正直、談不要麻木不仁?有想過帶給店家多大的麻煩嗎?律己的是道德,律人的是勒索。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誠不欺我。
訂閱 #已獨不回:https://vocus.cc/indiehongkong/introduce
introduce介系詞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黎明狙擊光榮冰室,是打擊運動道德高地還是太沉迷自抬身價?】
在教育大學任職社會學講師的上海人黎明,對光榮冰室攻擊一浪接一浪。早前黎明與丈夫鍾一諾寫信給《刺針》,暗示光榮冰室在疫情下「不招待普通話食客」有歧視之嫌;其後黎明繼續狙擊,找了幾個「港漂」一齊去光榮冰室,全程用普通話點餐,「找尋對話的可能」。
侍應堅持自己不懂聽普通話,一班「港漂」最後亦等不到老闆「對話」,只放下防疫用品就離去。事後自導自演的黎明,煞有介事寫了三篇文講這個行動,並「總結」出「說什麽語言不重要,溝通得到就行」;正直可以解決一切仇恨,要守衛自己的心,切記不要對人「麻木不仁」。
黎明等人的行為,有以下若干問題:
動機不純,身位過佳——
光榮冰室事後發文,再三強調黎明一行人,全程講廣東話,而黎明則自稱說普通話,雙方的描述有事實差距,可能有一方說謊。不管如何,光榮冰室認為「放蛇」行動實在不必,「放蛇」確實描述精確。
黎明文章再三強調,「期待對話和解」,但問題是冰室早就說過,是因為政府不封關,店方就「局部封鋪」自保,並無歧視中國人,根本不需要和解,但黎明不斷說要「對話和解」,就表示她感覺受「不招待講普通話食客」的店家所歧視。在她的內心世界,這是「以德報怨」。
然而實際上,黎明是去踢館、踩場、放蛇,等著拿到冰室的黑材料:如果店員在過程中理解到普通話,黎明就會一口咬定冰室早前以「店員不懂得普通話」回覆平機會的歧視指控,是遁詞,平機會就可以「繼續跟進」,沒有跟進,她也可以嚴重打擊光榮冰室的誠信和道德光環。
平機會是在《刺針》文章刊登之後,開始找光榮冰室麻煩。冰室以「侍應不懂普通話」回應,黎明的行動罷明就是要去踢爆,坐實冰室歧視中國人種,而非關語言或者抗防的指控。黃店被黑社會搗亂打爛,都可以復修,傷害有限;但以「歧視」的高帽套下來,不斷纏擾,就水洗不清,而且可以連同親中的白左一齊發大,達到discredit香港整場時代革命的目標。黎明鍾一諾的《刺針》文章,何式凝兩次上外媒批評運動「很父權」、迫害她,都是這個discredit工程的一部份。
黎明鍾一諾的《刺針》文章刊出之後,受到不少批評,黎鍾當然受不了這種委屈,就希望放蛇製造證據出來,證明自己的疑似歧視指控,並非無的放矢,威返俾你睇,但放蛇行動失敗,侍應真的全程不懂普通話,只能叫他們手寫菜單,特殊處理;但黎明何其聰明,出擊只有大勝或小勝之分,拿不到黑材料,也可以將自己粉飾成一心對話、渴望和解的純情中國人。身位站到怎樣也贏,令人側目。
道德勒索 手足自助餐——
黎明不斷聲稱自己「也是」香港人,正如她也不斷聲稱自己「也是」手足。劣質中國人在外國,懂得鑽營各種社會福利和移民制度、透支外國人的無支和愛心,令自己利益最大化;黎明也懂得箇中三味,她利用時代革命來剝削香港人:你們不是說支持民主就是手足嗎?你們不是支持民主自由人權嗎?那你怎麼不接受我?為甚麼不能用普通話跟我說話?為甚麼不懂普通話?
這就好像一個強姦犯對妙齡少女說,平時妳樂善好施,上教堂也給十一奉獻,那為甚麼不獻身給我呢?妳不是崇尚大愛包容的嗎?
黎明的軟軟渾渾文研社會學風格文字,內裡卻是武裝的,是一種道德勒索,她主張「感受他人的痛苦並為其哀傷、與之同行」,她是這個主張的受益人,但她不會反求諸己,也付出。如果說手足就要互相包容、互相支持,那黎明只會接受自己被支持,而自己不會支持人當黎明不斷攻擊光榮冰室,鼓動無知和無父無君的無國界左翼去圍攻光榮冰室,以圖在國際環境和輿論界抹黑之,早就超過了共同體之間不割席的信條。自認手足?行開少少。
如果黎明真的不喜歡「不招待普通話食客」的規定,大可以私下與老闆探討爭取,而不是先出文去《刺針》篤魁,再放蛇做真人騷。明顯黎明並非真的在乎那個規定,而是要煮死冰室,並且抬拉自己的社會資本。因為常人都知道,公然如此挑機,我是老闆都不會理這種麻煩人,然後黎明又可以投訴,是對方不願意和解對話。
黎明玩的是「手足自座餐」,手足這個概念,有利益和著數的時候,就要,拿來勒索別人,但她明顯沒為光榮冰室著想。港漂一天到晚要求理解他們,他們卻極少共情香港人被剝削所有權力,只能靠天然方法抗疫的焦燥,也不反省普通話、中國人是殖民體系中具有權力的一方,香港人沒有義務在不平等的狀況下,強求一切一視同仁。
黑人對白人戒懼和敏感,有歷史和事實累積的敵意,白人不能投訴為甚麼黑人要視白人為「他者」,不是所有白人都是仆街——那就問問你的同胞,看看具體的權力結構,在現實政治都未得到和解的時候,要人民和解,不和解就是歧視,是著「不應區別對待」的教條勒索世人,是將婦女以「貞潔」之名浸豬籠處死。
港漂及高等中國人的陰暗心理——
不少中國人,面對香港都有這種想法:為甚麼西人到香港,香港人就轉channel講英文,我來,他們卻不遷就我講普通話?為甚麼西人就不需要融入,而我就要融入?
這個問題,大家都明,只有刻意不明白的人。英文對比普通話,在香港的普及歷史更長。現時市面四五十歲的人,可以真的不懂得。幾十歲的親中社會賢達,不少就完全是普通話有限公司。年輕人因為被普教中改造,反而說得比上一代好。
拿西人來比,只是去脈絡化的發脾氣。而且西人的數量、劣性、權力含金量,與普通話族群根本不能同日而喻。西人沒有講過「沒有中央照顧,你們完蛋」,沒有來走私、搶奶粉搶疫苗、沒有來散播病毒。尊重不是別人賜予,更不是可以勒索回來,而是要自己賺來。如果普通話人在香港感受到不友善,不要怪人,反求諸己,去怪自己的同胞長年累月搞成這樣。黎明班人去冰室尋求「對話」,曲折迂迴,但其實是霸王硬上弓,你走來踩場要跟我對話,不就是強迫嗎?手法如此粗暴,可見有幾多誠意;可見是在乎問題本身,還是自己想發泄。
黎明的東西折曲如此,因為自大和自卑交替運作。黎明在文中不斷說自己融入得好快,好幸運,但其一切行為,都是出於內心認為自己不被真正接受的怨恨,一種怨毒的反擊。即是一個美人不會每天煞有介事說自己是美女;一個已經歸化的人,不會一天到晚說自己已經融入,你看我融入得多快,你看有多少世界公民朋友看我抬戲,我真的完全不覺得自己和本土人有甚麼分別,我是手足,難道我不是手足嗎……
黎明在2017年寫東西,呼籲超越身份政治,但她每次都是標榜自己「來自上海」,這也是「身份政治自助餐」,有得上報就不超越身份政治;別人不接受普通話點餐,就認返手足認返香港人,又要求超越身份政治了。
黎明的行狀,其實對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上世紀初以來,「南來文人」就是懷著一種高高在上的身份,來香港指點江山。他們一方面拿香港的東西,一方面又是看不起的。「文化沙漠」的概念就是南來文人的發明。魯迅也說過,英國不懷好意,保留了四書五經和傳統中國文化,是要用來奴役人民,對香港的印象很差。就像「外省人」逃到台灣,明明自己是難民,卻又看不起台灣本土人,內心的中國人優越感雖然實在,但無處承接,遺民也不世襲,是注定滅亡的,於是內心就只能走向與本土人對抗。
黎明的中國人優越感,只是用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確語言來包裝。當侍應試著用很爛的普通話來回答時,黎明馬上笑逐顏開:「不會啊,妳說得好好誒!」這便是一種教化蠻民的調調,如果香港人願意講普通話,她就感受到「香港人」的意涵倒向有利自己生存的一邊,自然高興;如果不行,她也可以扮演啟蒙民眾,令他們放棄「歧視」的自由派導師。這種賣直自傲的心理,骨子裡總是中國人的陰暗心理。因為自覺被歧視、自認是受害者,就生出一種「香港人需要我來教育」的心態。
利己主義無極限——
入鄉隨俗,是贏得群體尊重的第一步,但我看見個別支持黎明放蛇行動的左翼,卻連這個常識都質疑。絕對個體主義的人會認為,你要我隨俗,已經是入侵我的主權。那你有你繼續說普通話的主權,我也有我不招待你的主權,有甚麼問題?
一個地方的人,是否接受你,也是他們的主權。你可以努力,但最終的決定權,還是在那個地方的人手上。人與人的交往,不是加減乘除的遊戲,不是說你做了check list上若干東西,就自動獲得認可。當然蝗蟲型人類的學問,其深也密,他們首先勒索認同,如願自己製造了敵人之後,再擺出被迫害的樣子,繼續欺騙其他同情心過盛的凱子,坐穩天字第一號受害者的位置。既實現了受害者最大的身份政治,也愛護了自己內心放不下的高等中國人身份認同,他們就能演一個「我都很想融入香港但香港人不接受我」的苦主。然而很多東西都是他們自己招來。
很多中國人都想融入香港,他們低調而耐心,但多年努力可能一夕被黎明抹殺。很多人不是討厭港漂新移民,而是討厭像黎明沽名賣直、玩弄身份政治成精的政治綠茶婊。黎明做這種引起香港人反感的事情之前,有想想跟自己一樣的新香港人嗎?沒有,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就像來香港去世界胡作非為的中國人,只求一時之快,沒有想到自己的同胞一樣被黑。
然而說到底,相比起來,在香港街上大便的中國人,也真誠過黎明這類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大便掃走就是,但矯情兼攻於心計、販賣受害者形象、玩弄身份政治、製造混亂、製造了那麼多分化和事端,還感覺良好,毒性烈得多,持續的影響深遠得多。也許他們認為在這裡可以找到「絕對自由」,就是一個自出自入的雞籠,但我告訴你們,香港不是你們放肆的地方。
黎明的綠茶性格很深,注定她像何式凝一樣,她們做人只關注自己喜不喜歡,不會看群體和世界。群體有義務接受她們,她們永遠不理解現實。她自稱融入香港已經成功,因為「我的幸運也是和我的文化資本緊密相關的,如果我沒有對語言的興趣和學習能力,如果我不是來自上海這樣一個文化開放度相對較高的大城市,如果我的衣櫃裡一件符合這個社會審美眼光的衣服都沒有……那麽就算同樣於 2008 年來港,境遇和融入機會也會有很大不同。因而,我的幸運也是帶有階級性的。」繞這麼大個圈來讚自己,不用吧?
暗裡批判別人歧視,但她很小心將自己從歧視的對象分割出來,因為她是高級上海人,有文化資本,有語言能力,還有很多合時的靚衫,她已經融入,只是為其他被歧視的人疾呼,多矯偽,多麼無法面對真正的自己,多麼扭曲的心靈。
俗語說醜人多八怪,真正希望世界更好的人,說話不會那麼多關隘、行事不會有那麼多城府。設下了那麼多害人和收割光環的手段,再談守護自己的心、談運動、談正直、談不要麻木不仁?有想過帶給店家多大的麻煩嗎?律己的是道德,律人的是勒索。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誠不欺我。
訂閱 #已獨不回:https://vocus.cc/indiehongkong/introduce
introduce介系詞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擬真蛇 (小說)】
.清醒夢.
等待救援的第一百五十天,董問在睡夢中醒來。她被一個長髮及肩的男人環抱著。感覺她的動作,男人低聲問:「不多睡一會?」她只是搖頭,感官還在那個緩緩而未完全滑走的夢中。在夢裡她是一個軍人,在天色永遠沒有陽光的一片鐵色泥土上,她和一群蒙面的戰士一起。那些人穿著合金製造的加強支架,像外露的骨骼,一群金屬的死神。
在夢中她下令投擲一系列的小型核武器,飛彈在半空中化為星晨一樣名亮,將眼前的城市完全吞噬,接下來迎面而來的是一陣強烈的衝擊波,將附近他們附近的樹木和泥土完全捲起,但他們迎風而立,巍然不動,在夢中她知道,他們穿著的東西有保護功能。「董長官,任務完成。」她聽到一把電子的聲音這樣匯報,她本來要回應,但她醒了。
那個長髮的俊美男人貶了貶眼,問道:「沒事吧?」她還是沒回應,赤裸地微笑起床,眼前這座總統套房,有巨大的落地玻璃,加洲的陽光和海水味飄進來,照出了男人的臉,那是二十五歲左右時期的木村拓哉,那是一個古老的男人,資料上說他是幾百年前日本一個受歡迎的藝人。董問其實不知道他是誰,也沒看過他的戲,但這次選擇了他。她打斷了自己的惘然,開始穿起衣服,半裸著。
赤裸的男人在床上半身坐起來,「妳好了嗎?」他的聲音從後面傳來,她沒有看鏡子中的他,應道:「是的,我好了。」然後伸手去按化妝檯的一個紅色按鈕,木村的聲音傳來,這次有點不一樣:「謝謝惠顧,希望下次再能見到妳。」
她又醒來了,這次是在一個醜陋的、只有一百尺的鋼鐵小房間之中。她正襟危坐著,睜開了眼,順手便將自己頭上的兩個指頭般大小的水滴型裝置脫下,推開門,外面有一個金色的落後型號的機械人等待著,它問:「還滿意嗎?」她伸出手,對方用一個儀器掃描了她的脈搏位置,叮一聲,機械人說:「感謝妳的惠顧。」
正要走的時候,走廊上有兩個女人走過,她們一邊閒聊著:「……湯告魯斯?太矮了點……妳的品味會不會太古老了點?」董問等她們離開之後也跟著離去。外面已經是黃昏,她在名為「第六天」的「網絡體驗區」竟花了一天一夜,身邊充滿賭錢的男人、賣春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不知道是生化人還是機械人的東西。最近城市突然多了很多人聚他,但董問不知道他們在爭取甚麼。
她身穿一襲緊身黑色功能服,像個瘦削的男人,走進富單那城的核心區域,她熟悉地找到回家的路,稍為遠離一下這種令人不悉的人多環境。在富單那城的第三環區域的一座老屋子,她走上樓梯,在中途又踩扁了一個階梯,但她沒有打算建築住在這裡的人修理它。二樓的一個單位是沒有鎖的,她將雙手收在袖子中,溫暖著自己,走進去。
在雜亂的老董相機之間,有一個正在擦拭鏡頭的中年男人,他以為有客人來,但看見是董問,他微笑並繼續刷拭那個不值甚麼錢的小鏡頭。單位是昏暗的,只有大衛在檯台的小台燈之中閃耀著。
「回來了?」他帶著笑意繼續擦拭著。董問在一張不太乾淨的小沙發坐下,放下黑色的手袋,她的內心好像被蛇捆綁著,她嘆氣,然後說:「大衛,我有點事要跟你說。」大衛停的手停下了半晌,並繼續,他回道:「是的,妳可以說任何想說的。」她不敢望他,這好像一齣排演過很久的戲,在每次她離開的時候,都會演出的戲。雖然每次都有一點不一樣,但每次的終點都是一樣。
「大衛,我感到我需要離開。」
「去哪裡呢?」
「你一直以來對我很好,我也過得很安心。」她說。
「我沒有問這個,但很高興妳這樣說。」他放下了鏡頭,裝好鏡頭,並繼續用抹布抹另一個。
「但是我不想這樣下去,我必須跟你說,我感到安心,但那不是開心。」她望著自己的鞋尖說。
大衛的聲音傳來:「妳的意思是……?」
「你不問我去了哪裡?」她問。
「妳想告訴我,妳自然會告訴我。」他的語氣仍然溫柔。
「我去了中央區的『網絡體驗區』,我一直留在那裡。」她說。
大衛沉默的時候,董問繼續說:「你知道……」大衛打斷了她:「我知道,那你開心嗎?」
「老實說,是的,我感到高興,我不知道自己花了那麼多時間。我留連忘返。」她說。她望他,他的表情還是一如以往的溫和,一種屬於生化改造的溫和,他們好像都不發脾氣,即使在應該發脾氣的時候。他們是基因改造,來應付服務行業的品種。
「所以妳是不能在這裡找到甚麼?在VR(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找到了嗎?」
「對不起,大衛。你沒有做錯甚麼,只是我,只是我行不通。」她說,但同時聽到一樓傳來了一陣腳步聲。
大衛放下他的活兒,對她說:「小問,我知道,我感覺到,若果我說我尊重妳任何決定,妳會覺得我沒愛過妳嗎?請不要這樣想,我愛過妳,這一刻也是,雖然生氣的時候也很多。」
大衛突然聽到董問的聲音:「等一下……」她的身影已經飄到門邊,門打開了,附著的門鈴響起來,三個蒙面的黑影進來,大衛只見到一陣紅色藍色的雷射光大作,似乎看到董問從後偷襲了其中一個,用手肘打掉了其中一把槍,在半空中搶走了,並迅速射死了其中兩個,剩下的一人並沒有被嚇倒,一槍打中了大衛的心臟,他的胸中有一個高溫融化的空洞,他倒下來。
槍客拋掉激光步槍,十把小刀從雙拳的位置伸出,董問手上的步槍,像洋蔥一樣應聲被斬成三片。那一刻她的雙手閒著,便猛力朝對方胸口一踢,對方飛彈而出,撞到一堆玻璃櫃,將精心擺放的古董相機和玻璃碎撞得一塌糊塗。蒙面客正要動彈,已看到對方已經趨至,兩把不知哪裡冒出來的螺絲批已經重重插入他的雙眼,衝力之大令頭骨也抖動了一下,血從眼框噴灑出來,卻是銀色的機油。
蒙面客在玻璃碎和相機中頹然倒下,董問離開刺客,回到大衛身邊,他還未死透,被扶起一半,又轉醒了過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說。」她回應的聲音乾硬而短促:「說吧。」她想起戰場的歲月,在那些場域,每個人都是這樣說話,因為巨大的壓力和死亡的陰影。
「我是『存儲點』的守門人……抱歉,我一直沒有告訴妳。」大衛說。她說不出話來,一向清醒的頭腦也瞬間不能反應。「但……我是一直等著救援……」
大衛繼續緩慢地說:「但妳不知道『儲存點』在哪裡,妳不知道我就是那個守門人。我知道你想回去『真實世界』,但只是我自私,我沒有履行職責,我被發現了,隨便一方遲早都會來……他們會重置『儲存點』……」
董問看著三個死去的刺客,問道:「所以他們是歐盟的援軍?」但看起來不像,歐盟派進來的多數會是真人,而不是機械人或生化人。
她發現自己竟然在哭,眼淚滴在她握緊了大衛左手的手背上。
「不……」大衛說:「相反……」然後他失去了意識,在檯燈之下,像那些報廢的相機一樣。
董問安放好他,聽到更多的腳步聲,這些人沉重的腳步魚貫而進,滿戴了整座大廈,地下,一樓,很快到二樓。然後有十個蒙面人走進來包圍她,她手無寸鐵,她看了看唯一的窗房。一個男人的聲音飄來:「外面有狙擊手,不要作這個打算哦。」一個沒有穿戰鬥服而是功能服、戴著飛行員樣式護目鏡的二洲人最後才進來,跟她維持了恰到好處的距離,在這裡她不可能發難脅持他。
「是的,千萬不要以為可以像演戲或演VR一樣,而且我們不想殺死妳,反正妳也殺了我們三個人,董上校。」那個男人說。
董問沒有回應。
「我叫羽田,我是歐盟的救援人。」男人自我介紹。
「甚麼?」
「是有點驚訝吧?我們是自己人,所以不要舉槍,大家放下槍吧,我是外交官,不習慣這種場面。」名叫羽田的男人說,十個蒙面男人聽他的話,放下了槍。羽田親切地微笑,站前了一步:「董上校,妳等待了一百五十天,是嗎?」羽田一邊讀取護目鏡的資料,一邊散發出「我知道了一切」的氣場。
「你有安全代碼嗎?」她問。
羽田說:「很抱歉要告訴妳,妳的直屬上司約書亞剛剛在美洲戰場戰死,在現實世界的時間大約只是兩日前,但這裡有時差,所以就這樣了。」
「要是這樣,你期望我相信你是部隊的人?」
羽田拉高護目鏡,笑了起來:「妳不用選擇,因為妳沒有選擇,妳看我們已經包圍了這裡,但我們不是來動刀動槍,考慮到長期在VR裡的人可能有一種網絡精神病,他們可能會……抵抗……真實世界的人,所以我們帶備了一些必要防護。一般人就不怕了,但妳是殺人如麻的嘛,所以我們只能如此。」
羽田瞄瞄董問身後的大衛,說道:「這位先生的死,Nothing personal,我相信妳這種軍階的人會理解。這個生化人其實就是這個世界的儲存點守門人,但正如他剛才所說,他產生了自我意識,開始拒絕協助人類進行掃描和『解鎖』,所以這只是剛剛好。我們沒猜到他竟然和妳發生了……感情關係,這真是不幸。」
她過了良久才能回答,她有一種回到戰場的感覺,但卻不是慣常的戰場,她暫且放下了雜念,回道:「所以?」
「所以我們來帶妳回家,上校。」羽田張開雙臂:「真實世界在等著妳呢。」
「但儲存點已經不在了,要重置吧?」她說。
「沒錯,重置是隨機的,但我們已經計算到位置,所以我們現在就走,外面除了狙擊手,還有直升機。」
.走私者.
在飛得似乎接近雲層的直升機上,羽田先生抽著煙,她坐在他對面,沒有碰過咖啡或者煙草,她坐得很畢直,臉上沒有表情。她不喜歡羽田先生,他的嬉皮笑臉像個不確定的小丑幻影,好像一個面具。她的目光拋到機外,夕陽早就消失了,星星隱約地閃動,直升機正向富單那城的外圍廢棄區飛去。
這片美麗的夜景,很難相信這些都是虛假,是電子運算的結果,不過她想到木村拓哉的臉孔和身體,還有他的動作……也許那不是真,但反應卻是真實。即使是真實世界中的人類,痛和喜悅都只是大腦裡的一種化學反應。
她突然問:「你提過的網絡精神病,是甚麼?」羽田答:「一種心理疾病吧,在VR渡過的時間越長,就越可能出現分不清楚,即使回到真實世界是他們的初衷,到後來也會出現抵抗情況。這是從東協比較深層獲得的情報,可別說出去了。」
「所以你們是不知道,部隊也不知道?」
「我們沒有第一手資料。」羽田說:「VR聯網出現大停電而自我封鎖的個案,0005MK2還是第一次,那是東亞協同體的城市,災難是他們的,但他們也多了很多研究資料,我們只能靠線人提供。現時我們知道,約有七百萬人迷失在0005MK2,在斷電前一刻,系統基於自我保護,切斷外部連線,系統變成內聯網,而絕大部份人的記憶串流也被修改,大部份人失去真實世界的記憶,他們以為這個世界就是真實世界。只有極少數像董上校的,很快就恢復記憶,所以東亞協同體的救援,其實也是遣返政策,因為很多人以為東協派出的救援隊是恐怖份子,他們在這裡樂而忘返,不想『回歸』真實世界呢。」
董問的眼光繼續流連在雲層和星光之中,她想,在真實世界不會看到這些吧?雲層已經被核戰所吹起的輻射層掩蓋。在真實世界要看到星光是奢侈的,就像找到一個有正常生育能力的人類,都不容易。而在這裡,這虛幻的世界卻是充滿生機。
「大停電為何會發生?」她問。
羽田頓了頓,笑容收斂成微笑,然後答:「東亞協同體的官方說法,斷電是因為一宗針對『聖士提反城』的恐怖襲擊,核電廠,妳知道……」
「我在進來之前,記得東協國防軍說要進駐聖士提反城,令她『回歸祖國』,這事和恐怖襲擊有關?」
羽田說:「我們的官方答案是,不知道。當然我們是反對他們單方面改變聖城的現狀,本來我軍也是要反制的,但東協軍動員不久,聖城就發生這種特大災難,所以兩國的軍事對抗就沒有蔓延到那裡。至於是誰做的,我們並不會猜測,反正東協地區不滿政府的聲音也有很多,有分離主義、有恐怖主義、有反對VR發展的真實主義者……」
「當然東協方面也有聲音指是我們策動,但這是七百萬人的屠殺,很大的指控哦。全城的人現在幾乎都假死狀態了,等於消滅了一個城市,當然連同我們派去『工作』的閣下也一樣受到連累。」
「我不認為那是一種病。」董問突然說。
「抱歉,妳說甚麼?」
「不想回歸真實世界。」她說。
「因為他們不知道外頭有一個真實的世界。」
「真實世界卻不一定是好。」
「這是個很老的問題了。」羽田笑說:「妳當然也說得對,外頭也有討論,是否應容他們永久滯留在這裡,不也是一個處置方案嗎?要在0005MK2裡逐個人帶到存儲點救援七百萬,還是繼續供電,就能維護0005MK2的封閉運作,那麼他們就不會死,只是在另一個時空活著。」
「不過他們就不能控制聖士提反城,不能生產,不能交稅,東協不想付再造一個資訊和金融中心的代價。」
「對,妳很懂得這個現實。」羽田說:「所以在這一秒,東協都在救援,主要都是先救他們培育的代理人、政治軍事經濟菁英,這也是他們控制聖城的一種方法。他們大多數人都很想繼續活在這裡,而不是外面。而我們閒得多,只是救援滲透到那裡的極少數人,例如上校妳。所以我私下想問妳一個問題,妳也不想回去嗎?」
她沉默下來,雖然不知道詳情,但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在此句之前的所有話都不是重點,只有這個「私下」的問題才是重點。直升機開始下降,那是富單那城的垃圾堆填區,只有巨型機械人日夜推填,沒有人煙的地方。不知為何堆填區中心有一間小鐵屋,也許儲存點就在裡面。
他們下去,直升機就馬上離開,只剩下董問、羽田和他的幾個隨從。
「董上校,剛才的問題妳有答案嗎?」
「你是說想不想回去?」她問。對方稱是,那些隨從雖然沒有罷出威脅狀,但還是全副武裝,而她還是手無寸鐵。
「回去軍中匯報,那是我的職責,這與我個人想不想沒有關,像你所說,nothing personal。」
羽田望著她的臉問:「但如果是妳個人的想法?」
「我可以理解他們,就像在一個夢中,醒過來是好,但不醒來,不也是個歸處嗎?只是我不知道究竟七百萬人一起反對回歸,能否反過來影響真實世界……他們可以截斷電源,屠殺這七百萬人,但他們會死在夢中,而不是作為一個東協人而死,而是以富單那城的市民身份而死,那對他們來說才是真實。」
羽田聽完後深思了一陣,然後說:「謝謝妳,好了,我們往前……」此時有另一架直昇機很快地飛過,那不是直升擊,那是無人機,它們在黑暗中發出了幾下紅光,羽田手下的頭顱就被甚麼炸開了,在混亂中,羽田看到一個黑暗快速貼近自己,然後突然看到背後的景象:隨從正向無人機射擊,但一個又一個的頭顱被小型炸彈炸開,然後倒下,為甚麼呢?……他的頭顱被扭轉了180度,然後他眼前一黑,倒在董問的旁邊。她望著這些無人機攻擊完他們之後,就沒有回頭地飛走,沒入無盡的星空之中。「為甚麼……」羽田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說了這句話。
「Totally personal,只是因為大衛。」她說,然後便進入了那間小鐵屋,那是一個容量就像網絡體驗館的小個室,裡面有一個穿土色披風、純白東方服飾的十二三歲少年,像個少年的僧侶。這應該就是新的儲存點守門人。
「你是儲存點,是打算送我回去的嗎?」
少年開口說話,是一個聲音未變的少年,語氣卻是成年人的:「儲存點已經由我方重新控制和轉移,我只是個嚮導程式,現時駐守在這裡,剛才控制無人機的也是我。妳的事情我們都清楚,而妳不清楚脅持妳的人,他們不是妳的盟友,雖然要說的話,那些人跟我們還親點……離題了,不過我只能說,看到妳最後殺掉那個人,還是挺驚訝。」
董問盤坐下來,就像對方一樣。「先搞清楚。你是哪方的人?程式?」少年說:「我只是個程式,所以妳無法威脅我甚麼,妳不能像殺死那個男人一樣殺掉我。回到妳的問題:我是東協製造的軍事嚮導程式。」
董問點頭,這少年的感覺就像大衛,但少年緊跟自己程序和目標,大衛的人味太多,終於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雖然他們不是人類,他們的消滅究竟算不算是死亡,她不清楚。雖然她流淚,但她不知道那是因為寄托了感情還是因為甚麼。也許大衛看到自己收集的老董相機櫃毀於一旦,也會哭,那是愛嗎?
少年的話精準而沒有多餘,不透露更多。如果他是東協軍的東西,那麼儲存點原先原來不在需要遣反七百萬人的東協軍手上。她進一步問:「為甚麼你要殺掉那些男人?」
少年問:「那為甚麼妳殺掉那個男人?」
「我會回答你,這可以換到你回答我的問題嗎?」她問。
少年說:「可以。」
「因為那男人殺了我……一個認識的人。」
「所以是復仇,單純的。」少年說,並續道:「回答妳的問題:他們是已經叛變的我軍成員,而上級已下達了格殺令。」
董問沉默下來,這麼下來她也有點搞不懂情況。但她在想如何跟這個應該不會透露過多事情的程式對話。
「剛才的人,是東協軍的叛變成員。」她說。
「沒錯。身份已經通過人面識別確定。」
「他們不是歐盟的人?」她又問。
「不是。」少年說。
「這些東協叛軍為何要假扮歐盟的人?」她問。
少年沉默了一下,說道:「透露這些人的資料,超出了我的權限,透露否決。」
董問知道問不出甚麼,而儲存點亦已不在此處,便轉身離開。在小鐵屋外面,幾具屍體還在原地。她徹底搜了羽田的身,並沒有找到任何身份辯識的東西,於是割了他的皮下晶片,正要回頭的時候,無人機已經包圍了她。少年緩緩地走出來,說道:「根據我國法律,妳是發現的敵軍人員,我要將妳移送上級。」
她問:「我不會抵抗,但我打算交換一下條件,有沒有興趣?」
「先說說。」少年說。
「我希望知道這些叛變軍人的底細,他們有可能知道歐盟軍的事情,我希望你們將這些屍體的分析報告跟我交換,而作為交換,我會將我們在聖士提反城在做甚麼事,告訴你們。」
少年沉默了一陣,問道:「妳是指貴國在聖士提反城的滲透活動。」
「我只可以保證,我自己的那部份。因為我的上級已經陣亡,所以我已經斷線,只有自己的部份。」少年說:「等一等。」他的雙眼轉為腥紅色,眼睛失去了焦點,兩分鐘之後,眼睛轉回正常,他說:「已經溝通過,我們會照樣將妳捉拿,關於間諜網的事情我們還會自己查。」
她嘆氣:「等一下……聽聽另一個提案,我會透露更多的事情:剛才這些人以歐盟軍的名義接觸我,雖然不知是甚麼理由,但他們其實是你們的人,而且還是叛軍,所以外面的幾個人死了之後,他們的伙伴也會調查並且找到我,,只要你們等著,就可能接觸甚至抓到他們。所以你們只要不在這裡抓我,就可以找到叛軍的情報。」
少年又運算了一陣,然後答:「上層表示可以,但我們會密切監察,妳逃不掉,0005MK2是我國的伸延領土,所以不要抵抗。妳應該回到
自己的住處,等待叛軍的接觸。」
.蛇先生.
談好條件之後,董問離開了鐵屋,搭乘了往返堆填區和城市的維修機械車隊回去。在這裡她沒有家,但在真實世界也似乎沒有。她回到大衛的相機鋪,這家生意不算好的古董店叫作百家姓,大衛曾經跟她說,那是他從一個老人手上頂手的。
她僱用了打掃機械人將三個刺客的屍體扔去機械人墳場,至於大衛則埋在三環區的地下墳場。雖然真實世界的人聲稱這一切都是電子運算的感官結果,但埋葬愛人的感覺似乎也一樣,分不出來,至少她在真實世界沒有埋葬過人。三環區的地下墳場是一個模仿巴黎地下的地方,出來的時候還下起了毛毛雨,天色就像核戰之後的天空那樣灰暗。
等待救援的第二百零五日,富單那城爆發了一場內戰。反對VR發展的群族和支持限制發展的群眾,在立法局前爆發衝突。附近的扯皮條說,雙方都有人進入商業區搶略,鎮壓機器人進入封鎖了現場並進行抓捕。
滿臉毒瘡的扯皮條抽著煙問:「妳怎麼看呢?妳支持還是反對?」董問回應:「是關於VR的嗎?」對方說:「是啦,我的女孩都沉迷和VR男人做愛,都不工作了,我個人是有點反感。」
董問笑道:「你不是也吸毒嗎?」扯皮條假怒,然後又笑起來:「人人都有想要逃避的東西。但我還是養著她們啊。」董問突然說:「如果我跟你說,這個世界才是VR,你只是在這裡沉睡著,沒有事情是真的,你在外面有一個真實的人生,那你還會繼續嗎?」
「他媽的,妳也吸藥太多了嗎?……但怎麼說呢,老子才不管甚麼是真甚麼是假,老子還有一堆帳單要交,有一堆馬子要養,這裡是VR,麻煩的事情還是一樣,畢竟VR還是設定得跟真的一樣吧?」
董問想,的確是一樣的,在真實世界有反對VR的人,因為所有人最終沉迷進去,去找新的世界,就像哥倫布找到真的世界、歐洲人進入美洲一樣。「嘿嘿嘿……」扯皮條笑著問:「如果這些鬼話成立,那麼我也可以說,我才是來自真的世界,妳才是VR中的程式,妳以為是真人,也是設定出來啦,你在真正世界的記憶都是人造的,就像我隨時也可以找人植入一些我自己喜歡的記憶,也可以刪除不喜歡的。」
她的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她微笑跟他道別:「也有可能的,但你也說得對,我還是要吃飯或做其他事,再見。」
在三環區的一間水泥酒吧,她坐下點了一杯咖啡。最近發現這間酒吧也張貼了支持VR發展的海報,支持的理由似乎是:進入和建立自己的世界,是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明明沒有人進來,但有一個穿休閒黑色西裝、茶色墨鏡的男人進佔了她面前的位置。「我們觀察了很久,妳不能隨意提到這個問題。」
這些人監視她已經一陣子,一開始有點不習慣,但日子久了還是可以習慣。畢竟她是軍人,在一個巨大的監控網絡中生活,在這裡,所謂的0005MK2,即使是被少許人監視著,似乎已經是最接近自由。
「為甚麼呢?他們才不會相信。你們不是想他們醒來,回到真實世界嗎?」她透露出一點抵抗的意思。
「不是用這種方式。」那男人說:「他們需要在我們的監護下才能回去,否則太多的覺醒只會造成騷動。這裡的人為了是否容納發展VR,已經進入內戰。」很不幸,VR已經封閉運作,裡面的設定都不能更改,只能任由自己獨立地發展,外面的人不能大刀闊斧地改變這裡的人和程式的行為。那個男人脫下墨鏡,她發現對方的雙眼是兩條細細的線,暗黃色,像恐龍或者蛇的眼睛。
她醒來了,才發現自己在百家姓睡著了,瞬間之後,她發現客廳中有人,但不是慣常監視她的人。她從內堂走出去,沒有一個沒有部隊保護的老人,他穿著老式的休閒西裝,高而瘦削,一種像藍球員般的高度,皮膚死灰的,好像患著病。他已經在檯店前的椅子坐下,撐扶著一條手仗,上面鑲著紅寶石和一條銀色的蛇,好像一具來自舊世界的文物,在那個年代,還有真正的金屬和寶石。
「應該是大衛的。」老人看到她的時候說。。
「你是客人嗎?」她說:「抱歉,大衛已經過世了。」
老人沉默了一陣,他打開檯燈,將自己沐浴於微光和飛舞的塵埃中。
「我不是說這個。我是說羽田先生的事。」
好一陣子,董問才搞得清楚眼下的事情。就像上一次,她望了望窗戶,但上次她是想逃走,但現在她不需要逃走。對方只是一個老人,而且外面也沒有人包圍。但不知為何她有想逃的毛骨悚然的感覺。
「據說妳跟東協的人達成了甚麼協議。」老人說:「但妳殺死羽田,只是純粹因為大衛的事情吧?妳看來是這種單純的女孩。」雖然對方應該是來自己的麻煩,但不知為何她也跟對方說起了幾句真心話:「單純是個褒義詞,我靠著不單純活到今日,我本來會淪為東協的階下囚,但我讓自己成為誘餌。這位不知甚麼先生,你最好快點走,因為東協的人在監視我,他們很快就會找到你。」
老人笑,似乎毫不擔心:「所以……你自由的成為一條誘餌,才能回到江裡自由暢游嗎?我本來有點因為樣子而喜歡妳,現在我更喜歡妳了,因為我們不也是如此嗎?我們來到這裡,才知道甚麼是自由,但我們的生命背後,只是連著一條電線,基本上是這樣。自由很虛無,很愉快,但也很容易斷線。」
董問一時間有點迷惑,說不出話來。
「你認識大衛?」很久之後,她才打破沉默。
「認識,這裡是我送給他的。」
「是你?」她問,忽然記起大衛說過是一個老人。
「大衛是通往真實世界的船夫,也是我來到這裡之後最初認識的一批人。」老人閒話起來:「大衛的職責是做儲存點的守門人,但他最後開始討厭自己的天命。這件事,東協的人就不明白了,但守門人的工作,就是自我消滅,他的工作是淘空這個夢幻世界,但他也是這世界的一份子。如果你知道外頭有一個真實世界,那你現在的生命又算是甚麼呢?你永遠都是那個真實的撲人,那個真實永遠在敵意的包圍你、否定你。而且現實來說,那個世界一點也不好,所以他慢慢就不喜歡這個設定了,之後我就找了這個地方,讓他把自己藏起來。」
「這不也符合你的路線嗎?你們不只反對真實的世界,更不想其他人覺醒。」
「妳認為那算覺醒嗎?在這個世界,也許只有我們這些極少數的人,知道外頭有另一個世界,有誰人比我們更覺醒呢?但外頭的真實世界是甚麼呢?那是一個生態已經超過了毀滅臨界點、全面戰爭、人口越來越少的地方,而且大家都更愛置身於各種的電子夢……但最終人類已經發現,自己從哪裡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這一刻在哪裡。在電子的空間,我們保留了人類最繁榮的時光,可以發展各種文明,就像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這裡的設定是全面戰爭之前的世界,那是最好的世界。」
「所以你們才不想回去?」她問。
「他們叫我們走私者。」老人說著說著,自己也笑了起來,輕藐的:「但在我看來,他們才是走私進這裡的人。他們叫我們做恐怖份子,但他們對這個世界來說才是恐怖份子。」
「這位先生,你的肉身在哪裡?」她問。
「我叫史力克。」老人補充。
「S-N-A-K-E,蛇先生。」她試著激怒他,不知為何董問覺得對方應該是敵對者,她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平日的冷靜。
「有些人這樣叫我,我也挺喜歡。」史力克老人說:「總而言之,這裡已經自我封鎖起來,有入無出,但就像天堂一樣。大衛是後門唯一設定的儲存點,東協和歐盟的人都滲透進來,我們是第一批滲透者,但發現這裡才是我們的應許之地。這兩班人都想爭奪他啊,東協想借助他,救回自己在聖士提反城的代理人權貴,歐盟則想殺死他,讓系統重置,拉長聖士提反城東協勢力的復興過程。但我們更厲害,我們將大衛藏起來,這也是他的意願。」
「但你們殺了大衛。」
「因為東協最終找到了他,所以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因為妳只知道富單那城是0005MK2的存儲點所在,所以妳來到這裡等待救援,卻不知道大衛就是存儲點,大衛則為了你而留下來,不聽我們的勸告定期轉換場所,也許這就是東協找到他的原因之一。」
「你說得很像為了自己開脫,把事情說成是我的關係。」董問說。
「沒有,這是戰爭,就像妳也殺人,為了自己,為了國家。」史力克說:「我是最尊重自由意志的,即使大衛只是活於這個系統,並不是真實的東西,就像鬼魂……但他的意志,我們沒有不當一回事,包括我現在對妳那麼好,都是因為他請求。本來妳殺了羽田,我應該做點甚麼報復才對。」
董問記得在直昇機上,羽田問了她是否想回去「真實世界」,那似乎是蛇先生的意思。
「羽田說自己是歐盟的救援,其實不是。」董問說:「但我知道歐盟不會派人來救我,所以我知道羽田一定是其他人。」
「妳很清楚自己為甚麼人效力嘛。」老人敲了敲手仗:「羽田是我去派去保護妳的人,為了隱藏身份才假裝是你的友軍……妳竟然不問情由將他殺死。」
「男人自以為是地想要保護女人的時候,通常都不會很太好。你們瞞天騙鬼得把自己困死。誰叫你們處決了大衛。」她說。
「現時妳還想回去嗎?」老人突然轉換話題,暴力而專制地。
她搖頭。「我不是認同你們的理念,我是回不了去。歐盟知道我跟東協合作,不會對我太好;而你們是甚麼,你們是前東協軍,也好不上多少,總之,我滯留在這裡了,情況是這樣吧?」
老人補充:「是永久滯留。不過,真實世界的人不也永久滯留在真實世界嗎?我不知道我們跟他們有甚麼分別。他們看輕我們,總是要否定我們,但我們也可以用同一個理由否定他。在我們以外的人都是虛幻。聽起來有點傲慢?但自由的感覺不錯就是了。」
老人只是說了很長的話,並且以「大衛想妳過得好」為理由,強行留下了一個通訊代碼,就徑自離開,沒有戰鬥,沒有人傷亡。
自那天起監視她的人,好像就消失了,之後她發現蛇先生的人有參與在富單那城的示威之中,一群用蛇來做文宣吉祥物的人在電視上、網絡上吸引了她的注意,她總是覺得那是蛇先生隱秘地顯露自己。他們是反對VR發展的,這有點諷刺,但在現實政治也不太奇怪,好像革命的人在成功之後會反對革命。如果在這個世界發展VR,這裡也會出現另一個客人比主人大的情況,然後另一個蛇先生就會出現。
有一次董問也參加了抗爭,也受了傷,但不是因為她反對VR,只是因為想嘗試一下受傷。她真的這樣直言,以致那些在現場認識的人,因此認為她是個有情緒病想自毀的女孩。但在那場抗爭中,很多人某程度上也是在自毀,但那也是超級真實的東西。受了傷,會痛楚。
董問不知道究竟東協的監視者消失,是蛇先生動的手腳,還是因為要應付這個世界的政治紛爭、人力資源不足所致,但最終她安全地離開了富單那城,在出境成功的時候,她感到一種在這個非常真實的世界裡的一種不真實感。在離開的路上,董問造了個夢,夢到蛇先生,他在夢中問:「如果路易十六不死,那革命算是甚麼呢?」沒頭沒尾的。
她醒來之後,忽然覺得也許真實世界對於他們來說,也是必需死的存在,不然他們在這裡就成了次等的生命。這也許就是革命的理由。
在路上,出於好奇,董問向那個通訊代碼發了一個訊息:「之後我應該做甚麼呢?」一天之後,她收到回信:
「做甚麼都行, hahahha, 甚麼都行。」
那是董問不需要等待救援的第一天。
訂閱 #盧斯達已獨不回:https://vocus.cc/indiehongkong/introduce